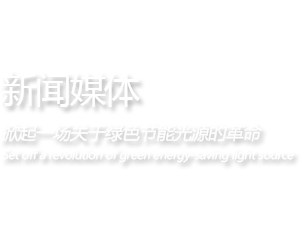兰普集团

新闻媒体

兰普刊物
琐忆
发布时间:2012年12月30日
那时候,母亲从江北嫁到江南,住在一个破败的大杂院里,院子里照例呈现出日趋颓败的光景角落里长年堆砌着落满灰尘的杂物,四面是爬满绿苔的青砖,屋梁下晃荡着不知何年何月废弃的麻绳。岁月在浑然未觉中无声地流驶,似乎只有乌黑瓦檐上那自生自灭的野草,一茬又一茬地诉说着日子的艰涩与世道的沧桑。母亲是农村户口,直到我七岁时,才转为城市户口。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这意味着我家必须在黑市上购买高价粮票,才能维系这漫漫的时日。日子仿佛大杂院那迫人窒息的矮檐,让人难以伸直腰杆。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为生计辗转奔波,她青春的容颜上过早地染上了岁月的风尘。
说来奇怪,这些年,幼年时那个挂满冰锥的冬晨总是无端地浮现在我的心头,感觉是梦里那一声遥远的呼唤,又仿佛是堂屋亮瓦上投下来那一束注满灰尘的阳光,难以割舍却又莫可名状。我们那个城市在长江以南,冬天却照例飘着雪。我能想象那个冬晨和母亲所走过的千百个清晨一样,依旧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起床,摸索着拉亮墙角那盏昏暗的白炽灯,然后用火钳将湿煤封好的火炉捅开,拎到大杂院穿堂而过的风口上。梳洗完毕后,火炉里就跳动着火苗。多年前,那一夜的北风裹着雪粒在院子里呼啦拉地旋了一夜,听着那声音,夜里心里绷得紧,清晨倒是一片宁静。母亲帮我穿好棉衣后,摸了一下我的手,抱我到门框边的小凳子上坐好,就下厨做早饭去了。我扶着门框,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那一刻的世界就折射在屋檐下的冰锥里,变得晶莹剔透又离奇梦幻。似乎漫天彻地都是一片白皑皑的宁静,不过也不尽然你看,那零星的雪花还迟迟不肯落地,好像依旧留恋昨夜的疯狂;即便是风中微微颤动的梅枝,也自怜惜昨夜在风中遗失的花瓣;更不必说那聒噪的麻雀了……
在清晨寒冷的空气中,我似乎能细微地感觉一切生命以有声的方式在宁静中存在,一丝会心的笑意从我心底流出。母亲这时从厨房走了过来,把我揽在怀里,紧攥着我的小手,接着又将我的手放在她的颈窝里摩挲着,喃喃地说:“你看你,手冰凉冰凉的……”。那一刻,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身体被我的手冻得有些瑟瑟地发抖,然而颈部动脉依旧强劲地跳动着,传递着生命的暖流。
随后几十年,即便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但只要是冬天寒冷的日子,母亲总喜欢握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只不过那双手从最开始的丰腴柔软变得枯瘦僵硬了。曾几何时,她握着我的手总笑着说:“嗯,很暖和,很暖和,好好……”她也许意识不到,不是我的手变暖了,而是她的手冷了。在母亲的意识里,我仍然是那个颤巍巍扶着门框看冰锥的小男孩,我生命的一切都融入了她的身心当中。
我来到这个世间,看见母亲做的第一份工就是在江边挑沙。那时,她就像一个时刻绷紧发条的钟摆,每天在家与工地之间来回摆动,一天四趟,寒暑不断。从我家到工地约有二十分钟,为了节省路程,母亲走堂过巷,就近穿插,待到工地如丝如缕地呈现在眼前时,我跟在母亲后面早已是疲惫不堪了。那时候,我不停地埋怨母亲走的太快,我几乎是小跑才能跟得上。也许她并没有意识到,我那时只是个五岁的孩子,她的一步抵得上我两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生活的重担如影随行,就在她脚后跟那儿挂着,似乎她只能向前快步走着,才能甩掉那些不堪的日子。
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皮带运沙,从长江上游来的沙船停靠在岸边,宛如一只僵死的昆虫,挑沙工象一群蚂蚁要在最短时间内将这只昆虫分解消化。整体分工错落有致,忙而不乱。两条一尺二寸宽的跳板从船头搭到岸上。舱内有三到四名工人专门负责铲沙,然后将装满沙的沙兜整齐地摆在船沿上。约有二十来个人排成进出两条队,一条进,一条出,蜿蜒几十米,一直到沙堆的尖顶上。每人肩上扛着扁担,轻飘飘地走上船头,将两个空兜子放下,挑起两个装满沙的兜子,然后颤悠悠地走下跳板。平地上前后两人间距约两米,沙丘上坡时前后却摩肩接踵,就这样一担接着一担,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约一顿饭的功夫,平地上就冒出个方圆二十米的沙丘,从沙尖顶到根部有两条脚印踏成的沙路,上坡深,下坡浅。这时,原先吃水很深的沙船如释重负,渐渐地能在水面上晃来晃去了。
母亲在江边挑沙整整十年,后来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托人帮忙,她才进了一家街道集体所有制的纸箱厂里做搬运工,虽然依旧是汗水摔八瓣的活儿,好歹算是有了份稳定的工作。日子如逝水无痕,似乎很难记清最初的原点。我印象中母亲有件红缎面的小棉袄,应该是她陪嫁过来的。那时候,因为上不起幼儿园,我只能跟在母亲后面,她上哪儿我就跟哪儿。冬天身上的棉衣厚,走不快,也只能拽着母亲的红棉祅向前奔着。日子久了,母亲的新棉袄被我拽出了个洞,呈把手状,向外稀稀拉拉地泛着棉花。
前年冬天我从外地回乡,和母亲在老屋里翻捡旧物,没想到那件棉祅还整齐地压在箱底,不知何时那个洞已被缝好。几十年前的琐忆潮水般涌了上来,那时母亲笑着,琐碎地说着往日里不值一提的旧事。原来,母亲的世界一直都明晰地挂在我们那个城市的背景里,一片残留在矮檐下的缀丝尘网,一个飘逝在阴暗阁楼里的梦,一串简单而凄婉的歌谣,这些都是我们卑微的灵魂不觉中千百次体会过的,以致我们本来明净的心灵蒙上层厚厚的风尘。那时,冬日的阳光正弥漫在大杂院里,日子以少有的明媚方式浮现出来,大杂院变得陌生而美丽,我只看见母亲的嘴唇在翕动着,似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感觉又回到了多年前那个挂满冰锥的冬晨,母亲是那样的丰腴而美丽,她的笑容就象眼前这冬日的暖阳,给我驻入永恒的温暖。这个女人用一种看上去近乎本能的坚韧与美丽,无言地诉说着岁月里最平淡的传奇。
“你在想什么”母亲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在想,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衣服”我心里有些发酸,声音有些颤抖。母亲笑了,屋顶的阳光正透过亮瓦,折射出七彩的眩光,映射在母亲美丽的容颜上。
说来奇怪,这些年,幼年时那个挂满冰锥的冬晨总是无端地浮现在我的心头,感觉是梦里那一声遥远的呼唤,又仿佛是堂屋亮瓦上投下来那一束注满灰尘的阳光,难以割舍却又莫可名状。我们那个城市在长江以南,冬天却照例飘着雪。我能想象那个冬晨和母亲所走过的千百个清晨一样,依旧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起床,摸索着拉亮墙角那盏昏暗的白炽灯,然后用火钳将湿煤封好的火炉捅开,拎到大杂院穿堂而过的风口上。梳洗完毕后,火炉里就跳动着火苗。多年前,那一夜的北风裹着雪粒在院子里呼啦拉地旋了一夜,听着那声音,夜里心里绷得紧,清晨倒是一片宁静。母亲帮我穿好棉衣后,摸了一下我的手,抱我到门框边的小凳子上坐好,就下厨做早饭去了。我扶着门框,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那一刻的世界就折射在屋檐下的冰锥里,变得晶莹剔透又离奇梦幻。似乎漫天彻地都是一片白皑皑的宁静,不过也不尽然你看,那零星的雪花还迟迟不肯落地,好像依旧留恋昨夜的疯狂;即便是风中微微颤动的梅枝,也自怜惜昨夜在风中遗失的花瓣;更不必说那聒噪的麻雀了……
在清晨寒冷的空气中,我似乎能细微地感觉一切生命以有声的方式在宁静中存在,一丝会心的笑意从我心底流出。母亲这时从厨房走了过来,把我揽在怀里,紧攥着我的小手,接着又将我的手放在她的颈窝里摩挲着,喃喃地说:“你看你,手冰凉冰凉的……”。那一刻,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身体被我的手冻得有些瑟瑟地发抖,然而颈部动脉依旧强劲地跳动着,传递着生命的暖流。
随后几十年,即便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但只要是冬天寒冷的日子,母亲总喜欢握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只不过那双手从最开始的丰腴柔软变得枯瘦僵硬了。曾几何时,她握着我的手总笑着说:“嗯,很暖和,很暖和,好好……”她也许意识不到,不是我的手变暖了,而是她的手冷了。在母亲的意识里,我仍然是那个颤巍巍扶着门框看冰锥的小男孩,我生命的一切都融入了她的身心当中。
我来到这个世间,看见母亲做的第一份工就是在江边挑沙。那时,她就像一个时刻绷紧发条的钟摆,每天在家与工地之间来回摆动,一天四趟,寒暑不断。从我家到工地约有二十分钟,为了节省路程,母亲走堂过巷,就近穿插,待到工地如丝如缕地呈现在眼前时,我跟在母亲后面早已是疲惫不堪了。那时候,我不停地埋怨母亲走的太快,我几乎是小跑才能跟得上。也许她并没有意识到,我那时只是个五岁的孩子,她的一步抵得上我两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生活的重担如影随行,就在她脚后跟那儿挂着,似乎她只能向前快步走着,才能甩掉那些不堪的日子。
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皮带运沙,从长江上游来的沙船停靠在岸边,宛如一只僵死的昆虫,挑沙工象一群蚂蚁要在最短时间内将这只昆虫分解消化。整体分工错落有致,忙而不乱。两条一尺二寸宽的跳板从船头搭到岸上。舱内有三到四名工人专门负责铲沙,然后将装满沙的沙兜整齐地摆在船沿上。约有二十来个人排成进出两条队,一条进,一条出,蜿蜒几十米,一直到沙堆的尖顶上。每人肩上扛着扁担,轻飘飘地走上船头,将两个空兜子放下,挑起两个装满沙的兜子,然后颤悠悠地走下跳板。平地上前后两人间距约两米,沙丘上坡时前后却摩肩接踵,就这样一担接着一担,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约一顿饭的功夫,平地上就冒出个方圆二十米的沙丘,从沙尖顶到根部有两条脚印踏成的沙路,上坡深,下坡浅。这时,原先吃水很深的沙船如释重负,渐渐地能在水面上晃来晃去了。
母亲在江边挑沙整整十年,后来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托人帮忙,她才进了一家街道集体所有制的纸箱厂里做搬运工,虽然依旧是汗水摔八瓣的活儿,好歹算是有了份稳定的工作。日子如逝水无痕,似乎很难记清最初的原点。我印象中母亲有件红缎面的小棉袄,应该是她陪嫁过来的。那时候,因为上不起幼儿园,我只能跟在母亲后面,她上哪儿我就跟哪儿。冬天身上的棉衣厚,走不快,也只能拽着母亲的红棉祅向前奔着。日子久了,母亲的新棉袄被我拽出了个洞,呈把手状,向外稀稀拉拉地泛着棉花。
前年冬天我从外地回乡,和母亲在老屋里翻捡旧物,没想到那件棉祅还整齐地压在箱底,不知何时那个洞已被缝好。几十年前的琐忆潮水般涌了上来,那时母亲笑着,琐碎地说着往日里不值一提的旧事。原来,母亲的世界一直都明晰地挂在我们那个城市的背景里,一片残留在矮檐下的缀丝尘网,一个飘逝在阴暗阁楼里的梦,一串简单而凄婉的歌谣,这些都是我们卑微的灵魂不觉中千百次体会过的,以致我们本来明净的心灵蒙上层厚厚的风尘。那时,冬日的阳光正弥漫在大杂院里,日子以少有的明媚方式浮现出来,大杂院变得陌生而美丽,我只看见母亲的嘴唇在翕动着,似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感觉又回到了多年前那个挂满冰锥的冬晨,母亲是那样的丰腴而美丽,她的笑容就象眼前这冬日的暖阳,给我驻入永恒的温暖。这个女人用一种看上去近乎本能的坚韧与美丽,无言地诉说着岁月里最平淡的传奇。
“你在想什么”母亲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在想,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衣服”我心里有些发酸,声音有些颤抖。母亲笑了,屋顶的阳光正透过亮瓦,折射出七彩的眩光,映射在母亲美丽的容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