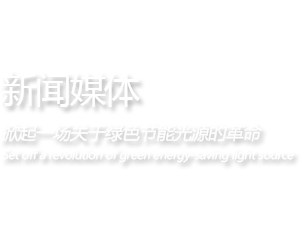兰普集团

新闻媒体

兰普刊物
盐盘村散记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31日
云卿:
十多年前我写给你的那些信笺大约已随风而逝了罢,那些残留在旧日里淡漠的哀愁,隔着时空的雾岚,感觉总是幼稚可笑的。当年你写给我的那几十封信,早已不知散落在何方了。时空变幻,烟云流散,前尘旧事已不可追忆。不过我总在想:那些承载着旧时悲欢离合的信件总还在这个世间流转,领受既定的缘分,即便是融泥化粉的宿命,那也是和光同尘沐风栉雨的历程,似乎本不必伤怀的。云卿,那时你说你会留在北京教书,当下你该当教授了吧。如今,在这个信息昌明的代,写信已成为无用的奢侈品。当年你总怨我不及时回信,其实现在我依旧懒散懦弱,只是两月前在湖南株洲出差,遗失手机,料想从此无法联络了,心里不免慌张起来。说来奇怪,我有你的手机号却从未给你打电话,因为即使不通话,心里依然有份淡淡的恬静,仿佛你是水里的月亮,虽不可及,却成一道风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许是自卑的心理在作祟,我本如一片落叶,在人世间听凭命运浮沉,实在没有权利扰乱你平静的生活。这样说来,遗失手机倒成了写这封信最直接的原由了。
二〇〇七年夏天,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原因, 我变卖全部家当,离开了生活了八年的深圳,辗转来到浙江,先在宁波呆了三年,后经朋友介绍来到现如今这个地方温州乐清。象我这样一个浪迹天涯的人,对于风景一向是淡漠无心的,然而这个叫乐清地方却让觉得有点“味道”。云卿,你知道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的雁荡山就在这里呢,听说很多影视剧取景也选择了这里。大约是“酸葡萄”的心理吧,我虽没时间去,却不觉得遗憾,料想风景好的地方却人头攒动,那点美的神韵和灵气大约也被挤得荡然无存了吧。
美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寻踪觅迹的,在于你是否有一双捕捉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美的心灵。你说呢,云卿!下午走在归来的路上,落了几点幽微的雨。起先一滴不偏不倚地落在眉间,一股略带腥味的凉意顿时在全身弥散开来,伴随着一阵心灵的紧缩,进而精神振奋,脚步也比先前快了。地上雨脚密集的时候,我恰好躲在一颗大树下,隔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先前还苍翠的群山这时却朦胧在雨中了。待到四下里是一片如麻的雨声时,心头禁不住袭来一阵如丝如缕的哀愁……唉,没想到这些年,我依旧是这样懦弱无用。不说了,如果你愿意,就听我说说身边这一方小小的人世吧。
云卿,我所生活的地方叫做盐盘工业区。这里原先是一个自然村落,如果把视野放得足够大,可看出三面环山,一面是大海。多年前,当地村民驱逐海水,日光晒盐,给淡如水的日子加入了耐人咀嚼的咸味,这也是村名的由来。近二十年来,经济大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吞噬了大片近海,当地政府填海圈地搞活经济,建起了高楼林立的工业区。以我多年遍历工业区的眼光看来,似乎这里的村民正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深圳当年渔民的生活模式,在日渐富庶的生活背后,慢慢地远离原来质朴的生活。不过,那可能是若干年以后的情形了,眼前至少还有这片海。傍晚涨潮前,村民放下竹篓和渔网;次日落潮时,能轻易捕获不少鱼虾壳类海产品。年复一年,盐盘村早市上,总是攒动着那些似曾相识的渔民们。当地有种在滩涂淤泥上滑行的“船”,(当地人把这个工具给予一种古怪的发音,这里写不出来。本地话很难懂,听上去像日语。不过也有例外,比方说他们把老婆叫萝卜。)大约有一米来长,八十厘米高,宽度却只能容磕膝盖,上部有双手可握的把手。渔民一条腿跪在船上,双手握住把手,另一条腿往后一撑,“嗤”得一声就溜出数米开外了。像你我自小在河边长大的人,恐怕是从未见过的。正是驾着这种船,能在滩涂上箭步如飞,眨眼工夫,什么跳跳鱼、蛤蜊之类的东西能捡一大堆。不过,这似乎是本地人的专利,外乡人恐怕只有泥里打滚的份了。傍晚时分,夕阳浮在大海尽头,绯红的晚霞贴在触手可及的睛空里,一位渔民肩扛鱼
网,拎着鱼篓,佝偻的身影红彤彤地印贴在大而圆的夕阳里。那一刻在我看来,生命的意义料想莫过如此了。
“日光流年不觉中永恒流驶,每分每秒都无可挽回。蓦然回首时,往昔的岁月似乎就印贴在褪色的门板上,亦沉淀于烟火氤氲的天井中……”云卿,这种感觉是我游历了盐盘村紫云观之后,随手在笔记本里记下的。从我工作的地方向西约行两公里,穿过一条窄窄的闹市,再拐过两个弄堂,马路对面的紫云观仿佛一位孱弱老人蹲在山脚下。道观不大,整体是凿空山脚岩石向内延伸而成。右侧两间厢房是招待香客的处所,左前方供奉三米来高的真武大帝。常年可见一个邋遢的中年道士坐在龛前打瞌睡,嘴角流着口水。寂寞午后,四方天井中驻满了白亮亮的日光,四周檐下流动着阴郁而明快空气。一捧残留在瓦檐下昨夜的雨水,两扇红漆剥落的大门,三根青烟缭绕的檀香,逝水般的岁月淤积成历史的横断面,这些平日里寻常的景象宁静地承载着我们自诩过的日光流年。云卿,这不过是一座年久失修的道观,但里面的情形和我以往生活过的四方大杂院却非常相似。我喜欢站在瓦檐下嗅着散发着淡淡霉味的空气,触摸着斑驳印迹的砖墙。感觉又回到了多年前的乡土上。在我而言,日光流年不单是人生的一种经历,也是一种难以去舍的负担。这些年心绪坏的时候,就想往昔时与你在一起的日子,似乎那一刻心里才能有片刻的宁静。这种“饮鸩止渴”的自我救赎的方式,侵蚀了我的灵魂,使我变成了一个行动上的懒汉,心灵上的懦夫。
从紫云观出来,外面依旧是车水马龙的集市。这是我们概念中喧嚣的集市,在我而言是见惯不惊的,不像郭沫苦在《天上的街市》里描述的那样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物品定然是世间没有珍奇…从街头到街尾约有500米行程,市场上囊括了当地村民所需的衣食住行。记得苏格拉底曾说,他所有人生经验及哲学都是从逛市场中得来,我佩服他的逻辑思想严明,却对这句话难以苟同,毕竟还是太吵,穿梭其中,感觉像是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心里总是惴惴的。云卿,如果你愿意,就随我到那些窄小霉晦的小弄堂里去转转吧。也许那里才代表日子本色的源流。
站在街市的中心,随意拐进一条只有一米来宽的民居小巷,两边低矮的瓦檐直逼心灵,头顶上的一线天显得格外高远。两旁是房门对开的出租屋,墙根处生长着时间累积起来的青苔,长得茂盛地方甚至有些许尿臊味。这时会传来小孩的哭声和炒菜的噼啪声,自然也少不了男女吊膀子声和嘶声力竭的流行歌曲声。感觉又回到了当年在深圳打工的情形,是那样的熟悉而亲切。这当然不是“风景”,更不是我们慷慨陈词中所说的“城市”,然而正是这些弱势群体们真诚而执拗地对待生活,挣扎于生命,日复一日地累积着生活的悲欢离合,用含混不清的和声唱着一曲悠长婉转的岁月之歌。说不清有多少卑微的生命混杂于我们这个浊世匆匆而来,而后无言地离去,在时光的河里惊不起一丝微澜,似乎只飘忽于褪色的壁板上和黑色的瓦檐下。不经意间,又化作黄昏里朦胧的灯火及山间细雨中迷漫的青烟……
云卿,这些年我逐渐习惯了在寂寞里咀嚼往日里那一丝甘甜,现实生活对于我似乎是隔膜而遥远的。一些埋在心里往日游丝印象,一片残留在瓦檐下的尘网,还有一位乍一相逢跟着又分了手的姑娘,这些都是我卑微的灵魂不觉中千百次深味过的。有时候心绪会无端地尖锐而执着,又茫然游移起来。此刻,窗外的晨光又明亮起来,那么日子在不经间又一次滑进了固有的轨迹。对于这个世界,我无话可说,只愿作个给灵魂唱歌的歌者……
喜欢诗人冯至写的那句诗,只要听了我的歌而流泪,不必追问我是谁。
言说不尽,道珍重。
十多年前我写给你的那些信笺大约已随风而逝了罢,那些残留在旧日里淡漠的哀愁,隔着时空的雾岚,感觉总是幼稚可笑的。当年你写给我的那几十封信,早已不知散落在何方了。时空变幻,烟云流散,前尘旧事已不可追忆。不过我总在想:那些承载着旧时悲欢离合的信件总还在这个世间流转,领受既定的缘分,即便是融泥化粉的宿命,那也是和光同尘沐风栉雨的历程,似乎本不必伤怀的。云卿,那时你说你会留在北京教书,当下你该当教授了吧。如今,在这个信息昌明的代,写信已成为无用的奢侈品。当年你总怨我不及时回信,其实现在我依旧懒散懦弱,只是两月前在湖南株洲出差,遗失手机,料想从此无法联络了,心里不免慌张起来。说来奇怪,我有你的手机号却从未给你打电话,因为即使不通话,心里依然有份淡淡的恬静,仿佛你是水里的月亮,虽不可及,却成一道风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许是自卑的心理在作祟,我本如一片落叶,在人世间听凭命运浮沉,实在没有权利扰乱你平静的生活。这样说来,遗失手机倒成了写这封信最直接的原由了。
二〇〇七年夏天,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原因, 我变卖全部家当,离开了生活了八年的深圳,辗转来到浙江,先在宁波呆了三年,后经朋友介绍来到现如今这个地方温州乐清。象我这样一个浪迹天涯的人,对于风景一向是淡漠无心的,然而这个叫乐清地方却让觉得有点“味道”。云卿,你知道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的雁荡山就在这里呢,听说很多影视剧取景也选择了这里。大约是“酸葡萄”的心理吧,我虽没时间去,却不觉得遗憾,料想风景好的地方却人头攒动,那点美的神韵和灵气大约也被挤得荡然无存了吧。
美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寻踪觅迹的,在于你是否有一双捕捉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美的心灵。你说呢,云卿!下午走在归来的路上,落了几点幽微的雨。起先一滴不偏不倚地落在眉间,一股略带腥味的凉意顿时在全身弥散开来,伴随着一阵心灵的紧缩,进而精神振奋,脚步也比先前快了。地上雨脚密集的时候,我恰好躲在一颗大树下,隔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先前还苍翠的群山这时却朦胧在雨中了。待到四下里是一片如麻的雨声时,心头禁不住袭来一阵如丝如缕的哀愁……唉,没想到这些年,我依旧是这样懦弱无用。不说了,如果你愿意,就听我说说身边这一方小小的人世吧。
云卿,我所生活的地方叫做盐盘工业区。这里原先是一个自然村落,如果把视野放得足够大,可看出三面环山,一面是大海。多年前,当地村民驱逐海水,日光晒盐,给淡如水的日子加入了耐人咀嚼的咸味,这也是村名的由来。近二十年来,经济大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吞噬了大片近海,当地政府填海圈地搞活经济,建起了高楼林立的工业区。以我多年遍历工业区的眼光看来,似乎这里的村民正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深圳当年渔民的生活模式,在日渐富庶的生活背后,慢慢地远离原来质朴的生活。不过,那可能是若干年以后的情形了,眼前至少还有这片海。傍晚涨潮前,村民放下竹篓和渔网;次日落潮时,能轻易捕获不少鱼虾壳类海产品。年复一年,盐盘村早市上,总是攒动着那些似曾相识的渔民们。当地有种在滩涂淤泥上滑行的“船”,(当地人把这个工具给予一种古怪的发音,这里写不出来。本地话很难懂,听上去像日语。不过也有例外,比方说他们把老婆叫萝卜。)大约有一米来长,八十厘米高,宽度却只能容磕膝盖,上部有双手可握的把手。渔民一条腿跪在船上,双手握住把手,另一条腿往后一撑,“嗤”得一声就溜出数米开外了。像你我自小在河边长大的人,恐怕是从未见过的。正是驾着这种船,能在滩涂上箭步如飞,眨眼工夫,什么跳跳鱼、蛤蜊之类的东西能捡一大堆。不过,这似乎是本地人的专利,外乡人恐怕只有泥里打滚的份了。傍晚时分,夕阳浮在大海尽头,绯红的晚霞贴在触手可及的睛空里,一位渔民肩扛鱼
网,拎着鱼篓,佝偻的身影红彤彤地印贴在大而圆的夕阳里。那一刻在我看来,生命的意义料想莫过如此了。
“日光流年不觉中永恒流驶,每分每秒都无可挽回。蓦然回首时,往昔的岁月似乎就印贴在褪色的门板上,亦沉淀于烟火氤氲的天井中……”云卿,这种感觉是我游历了盐盘村紫云观之后,随手在笔记本里记下的。从我工作的地方向西约行两公里,穿过一条窄窄的闹市,再拐过两个弄堂,马路对面的紫云观仿佛一位孱弱老人蹲在山脚下。道观不大,整体是凿空山脚岩石向内延伸而成。右侧两间厢房是招待香客的处所,左前方供奉三米来高的真武大帝。常年可见一个邋遢的中年道士坐在龛前打瞌睡,嘴角流着口水。寂寞午后,四方天井中驻满了白亮亮的日光,四周檐下流动着阴郁而明快空气。一捧残留在瓦檐下昨夜的雨水,两扇红漆剥落的大门,三根青烟缭绕的檀香,逝水般的岁月淤积成历史的横断面,这些平日里寻常的景象宁静地承载着我们自诩过的日光流年。云卿,这不过是一座年久失修的道观,但里面的情形和我以往生活过的四方大杂院却非常相似。我喜欢站在瓦檐下嗅着散发着淡淡霉味的空气,触摸着斑驳印迹的砖墙。感觉又回到了多年前的乡土上。在我而言,日光流年不单是人生的一种经历,也是一种难以去舍的负担。这些年心绪坏的时候,就想往昔时与你在一起的日子,似乎那一刻心里才能有片刻的宁静。这种“饮鸩止渴”的自我救赎的方式,侵蚀了我的灵魂,使我变成了一个行动上的懒汉,心灵上的懦夫。
从紫云观出来,外面依旧是车水马龙的集市。这是我们概念中喧嚣的集市,在我而言是见惯不惊的,不像郭沫苦在《天上的街市》里描述的那样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物品定然是世间没有珍奇…从街头到街尾约有500米行程,市场上囊括了当地村民所需的衣食住行。记得苏格拉底曾说,他所有人生经验及哲学都是从逛市场中得来,我佩服他的逻辑思想严明,却对这句话难以苟同,毕竟还是太吵,穿梭其中,感觉像是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心里总是惴惴的。云卿,如果你愿意,就随我到那些窄小霉晦的小弄堂里去转转吧。也许那里才代表日子本色的源流。
站在街市的中心,随意拐进一条只有一米来宽的民居小巷,两边低矮的瓦檐直逼心灵,头顶上的一线天显得格外高远。两旁是房门对开的出租屋,墙根处生长着时间累积起来的青苔,长得茂盛地方甚至有些许尿臊味。这时会传来小孩的哭声和炒菜的噼啪声,自然也少不了男女吊膀子声和嘶声力竭的流行歌曲声。感觉又回到了当年在深圳打工的情形,是那样的熟悉而亲切。这当然不是“风景”,更不是我们慷慨陈词中所说的“城市”,然而正是这些弱势群体们真诚而执拗地对待生活,挣扎于生命,日复一日地累积着生活的悲欢离合,用含混不清的和声唱着一曲悠长婉转的岁月之歌。说不清有多少卑微的生命混杂于我们这个浊世匆匆而来,而后无言地离去,在时光的河里惊不起一丝微澜,似乎只飘忽于褪色的壁板上和黑色的瓦檐下。不经意间,又化作黄昏里朦胧的灯火及山间细雨中迷漫的青烟……
云卿,这些年我逐渐习惯了在寂寞里咀嚼往日里那一丝甘甜,现实生活对于我似乎是隔膜而遥远的。一些埋在心里往日游丝印象,一片残留在瓦檐下的尘网,还有一位乍一相逢跟着又分了手的姑娘,这些都是我卑微的灵魂不觉中千百次深味过的。有时候心绪会无端地尖锐而执着,又茫然游移起来。此刻,窗外的晨光又明亮起来,那么日子在不经间又一次滑进了固有的轨迹。对于这个世界,我无话可说,只愿作个给灵魂唱歌的歌者……
喜欢诗人冯至写的那句诗,只要听了我的歌而流泪,不必追问我是谁。
言说不尽,道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