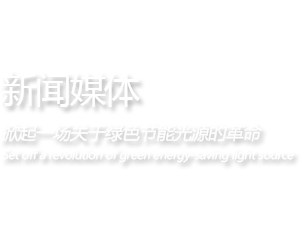兰普集团

新闻媒体

兰普刊物
雨天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30
三十年前的雨天是一片夹在旧书里的杏叶,散发着旧日淡淡的芬芳却又无从说起。
我所生活的城市是水边的一座小城,都市文明的车轮在这里似乎也还在滚滚前行,但只轧出浅浅的印迹。这些年在外谋求生路,每年回乡,看到的还是那些人,听到的还是那些事。大约是我思想隔膜或者麻木的缘故罢,即便是夜里深巷叫卖酒糟的小贩吆喝声,总感觉还是多年前长着娃娃脸、满面油汗、笑兮兮的那个人发出来的。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潮湿的小巷里来回振荡,一荡就是几十年。而屋角处绿油油的清苔,仿佛就是三十年前雨天里长出来的那一片。
我那时还是个六岁的孩子。当世界正幻着光怪陆离的光景向我蹒跚地走来时,而我却只能呆呆地坐在特制的方凳上。我因为一场大病,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站起来,脚就放在方凳前一块木板上。睛天我坐在四方天井中打瞌睡,雨天却是我的天堂。
我能嗅到雨前空气中水分子的味道。那淡香味混杂着一点点腥味的感觉,游离在我的神识内,使我目色迷离、欲仙欲醉。天上的雨滴是一个个调皮的精灵,他们笑嘻嘻地打着滚儿,前赴后继亲吻着大地上的一切。树梢上、瓦檐上以及不知名的角落里都是唇印,并且那唇印还会跳动地发出各种声音,响亮的如玉珠,沉闷的如叹息,还有那没有声响的,就落在我的心上。不一会儿,那四方的天井就挂了四扇透明的帘子了。我于是想站起来接那雨帘子,伸直了小手,颤巍巍地,怎么也不可能办到。那个瞬间,一双温暖的手从后面托住我的腋下,我回头一看,正是母亲。她明亮的眸子里正倒映着我纯真笑容,她也笑了。那一刻,她绝对是世间最美的女人。
那时,我们那个城市几乎没有超过六层楼的房子。上小学时,到一个同学家玩,他家住在市中心的六层楼上。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那样高的空间上,俯瞰我们这个城市。整个城市的基色是那种单调的土灰,歪歪斜斜的马路尽头就是我们家那种棚户居民的四合院子。从六楼远远看上去,象是一块块黑色的膏药胡乱地贴在城市的肌肤上。那些蚂蚁般来回攒动的人群和转来转去的车子,滑稽而紧张地演绎着生活悲喜剧。就在那时,又落雨了。
我站在高高的阳台上,习惯性地看着那雨渐次地落下,我们那个城市的底色变得明亮起来。那时,我感觉这天地间最公平的莫过于这细微而不可捉摸的雨了他们用一颗平常心在天地间飘荡,随时去领受那未可知的缘分,就在高耸的屋脊上,也在低矮的屋檐下,自然也在我的那片四方的天井中。谁能说三十年前那些落在我手中的雨滴不是因缘时会造成的呢?那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排黑黢黢的低矮小平房,在雨中默不作语地伫立着。而母亲那浅浅的笑容就幻作一片温暖的意象,在雨中被无限投影放大……似乎不堪记起的只是岁月里曾经有个小男孩颤微微地想站起来接那矮檐下雨帘子。
曾几何时,我的心在世俗的染缸里沉浮,变得尖锐而执着,又茫然而游移,似乎又是无从说起的。大约脱离方凳能站起来后,我对家境的困窘就有了概念。母新用厚重的汗水换取微薄的薪水,养活我和弟弟。象只燕子,在风雨飘摇的悬崖下搭了一个窝,然后战栗着身子为我们遮风挡雨。童年我虽然只能坐在方凳上,但没有丝毫的痛苦与自卑,相反,我感觉那段日子是一片镶着金边的白云,现在虽无法触摸,但意念中总是金灿灿的。
如今,母亲年岁大了,但世俗的烦恼并没有在她纯朴心灵上留下印迹,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她总是恬淡地笑
笑。我每年回家,总是要和她追忆三十年前雨天的情形。诸如:一到雨天,天井里就摆满了大盆小盆,大家总想省两个水钱。有个邻居还把缸搬出来,但可能是上天要惩罚贪心者,他往回搬的时候,居然把缸蹭破了。而母亲则用一支晒衣竹篙架在屋檐角,把水导引到屋里来,等等。我不停地说着,母亲并不插话,只是笑着。最后我问道:"妈,当年医生说我很可能站不起来,要瘫痪时,你是怎么把我扶起来的?"母亲发出一声幽微的叹息,并没有言语,随即嘴角漾出了一丝微笑。
文/严国栋
我所生活的城市是水边的一座小城,都市文明的车轮在这里似乎也还在滚滚前行,但只轧出浅浅的印迹。这些年在外谋求生路,每年回乡,看到的还是那些人,听到的还是那些事。大约是我思想隔膜或者麻木的缘故罢,即便是夜里深巷叫卖酒糟的小贩吆喝声,总感觉还是多年前长着娃娃脸、满面油汗、笑兮兮的那个人发出来的。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潮湿的小巷里来回振荡,一荡就是几十年。而屋角处绿油油的清苔,仿佛就是三十年前雨天里长出来的那一片。
我那时还是个六岁的孩子。当世界正幻着光怪陆离的光景向我蹒跚地走来时,而我却只能呆呆地坐在特制的方凳上。我因为一场大病,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站起来,脚就放在方凳前一块木板上。睛天我坐在四方天井中打瞌睡,雨天却是我的天堂。
我能嗅到雨前空气中水分子的味道。那淡香味混杂着一点点腥味的感觉,游离在我的神识内,使我目色迷离、欲仙欲醉。天上的雨滴是一个个调皮的精灵,他们笑嘻嘻地打着滚儿,前赴后继亲吻着大地上的一切。树梢上、瓦檐上以及不知名的角落里都是唇印,并且那唇印还会跳动地发出各种声音,响亮的如玉珠,沉闷的如叹息,还有那没有声响的,就落在我的心上。不一会儿,那四方的天井就挂了四扇透明的帘子了。我于是想站起来接那雨帘子,伸直了小手,颤巍巍地,怎么也不可能办到。那个瞬间,一双温暖的手从后面托住我的腋下,我回头一看,正是母亲。她明亮的眸子里正倒映着我纯真笑容,她也笑了。那一刻,她绝对是世间最美的女人。
那时,我们那个城市几乎没有超过六层楼的房子。上小学时,到一个同学家玩,他家住在市中心的六层楼上。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那样高的空间上,俯瞰我们这个城市。整个城市的基色是那种单调的土灰,歪歪斜斜的马路尽头就是我们家那种棚户居民的四合院子。从六楼远远看上去,象是一块块黑色的膏药胡乱地贴在城市的肌肤上。那些蚂蚁般来回攒动的人群和转来转去的车子,滑稽而紧张地演绎着生活悲喜剧。就在那时,又落雨了。
我站在高高的阳台上,习惯性地看着那雨渐次地落下,我们那个城市的底色变得明亮起来。那时,我感觉这天地间最公平的莫过于这细微而不可捉摸的雨了他们用一颗平常心在天地间飘荡,随时去领受那未可知的缘分,就在高耸的屋脊上,也在低矮的屋檐下,自然也在我的那片四方的天井中。谁能说三十年前那些落在我手中的雨滴不是因缘时会造成的呢?那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排黑黢黢的低矮小平房,在雨中默不作语地伫立着。而母亲那浅浅的笑容就幻作一片温暖的意象,在雨中被无限投影放大……似乎不堪记起的只是岁月里曾经有个小男孩颤微微地想站起来接那矮檐下雨帘子。
曾几何时,我的心在世俗的染缸里沉浮,变得尖锐而执着,又茫然而游移,似乎又是无从说起的。大约脱离方凳能站起来后,我对家境的困窘就有了概念。母新用厚重的汗水换取微薄的薪水,养活我和弟弟。象只燕子,在风雨飘摇的悬崖下搭了一个窝,然后战栗着身子为我们遮风挡雨。童年我虽然只能坐在方凳上,但没有丝毫的痛苦与自卑,相反,我感觉那段日子是一片镶着金边的白云,现在虽无法触摸,但意念中总是金灿灿的。
如今,母亲年岁大了,但世俗的烦恼并没有在她纯朴心灵上留下印迹,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她总是恬淡地笑
笑。我每年回家,总是要和她追忆三十年前雨天的情形。诸如:一到雨天,天井里就摆满了大盆小盆,大家总想省两个水钱。有个邻居还把缸搬出来,但可能是上天要惩罚贪心者,他往回搬的时候,居然把缸蹭破了。而母亲则用一支晒衣竹篙架在屋檐角,把水导引到屋里来,等等。我不停地说着,母亲并不插话,只是笑着。最后我问道:"妈,当年医生说我很可能站不起来,要瘫痪时,你是怎么把我扶起来的?"母亲发出一声幽微的叹息,并没有言语,随即嘴角漾出了一丝微笑。
文/严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