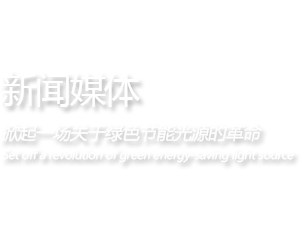兰普集团

新闻媒体

兰普刊物
繁星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30
小时候欢喜热闹,更爱新奇的玩意儿。夏夜躺在凉榻上,一面听大人们聊天,说故事,一面数着天上的繁星,记忆中最惬意的事莫过如此了。那些会说话的繁星个个都很调皮,它们躲过你的手指,避过你的眼神,比泥鳅还滑溜。你数着,数着,一会儿便不觉地茫然自失,而后渐渐睡去。夜半轻轻醒来,不知名的夏虫依旧幽然长鸣,丝丝的凉风带着夜气的潮润和清香正拂面而来。我的心活转过来,又开始数着天上的繁星了。一、二、三、四、五……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走进一片陌生的群山。不知从何时起,我已忘记了儿时数繁星这回事。也许是因为生计困顿罢,这些年尽在纷繁的人事中挣扎、流转,压根就模糊了四季的界线;也许是美的破灭只因距离太近吧没有光环的天使,没有雾岚的鲜花可谓是风景的缺憾。如今,我的心也许老了,在我看来,繁星只不过是宇宙中一团团进行聚变反应的高能量旋转体了。
也许幼年住惯了城市大杂院里漆黑的小阁楼罢,窗外间歇呼啸而过的车辆和夜行人沙沙的脚步,已成为生命中舒缓的摇篮曲。如今在这孤寂的山间夜里,却时常夜半无端地醒来。若是冬夜,还可就着落雪声或风过丛林尖啸声安然入睡,但这静得让人发虚的夏夜,亢奋的夏虫鸣叫似乎太琐碎了。我呆呆地坐在床上想,在这残月光景里,天上的繁星该别有一番意思罢。
沿着碎石阶迂迥而下,随意走进一片杉树林里。我终于又看见幼年时的繁星了!那些似曾相识的精灵们,有的睁着刚睡醒时朦胧的眼;有的喧闹地说,勿忘我;还有些忽隐忽现的,仿佛品味着人生的清凉。一会儿,我视野里繁星渐渐多了起来,有的离我而去。有的正向我飞来。我想,如果站在家里高高的平台上,定能摘到它们。然而,这异乡的土地似乎显得低沉些,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在流动的夜气里显得高耸而怪异。我不怕这夜的狰狞,因为我是爱夜的,爱夜每个有夏虫争鸣的角落,爱每颗灵性的繁星。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满月不见星,残月满天银。我想,眼前这情形应算得上是“满天银”了吧。此刻的月光不象旷野里的那样均匀而单调,而是流动并富于生气的。微风中的树梢摇曳着地上的月光,这微微颤动的亮点真象是抽象派的素描画,可产生天马横空的梦幻,也可让人寂然凝虑的思索。白天这几排经过人工刻意修整的水杉是刚劲质朴的伟丈夫,现在却有着婉若流水般的身影,自然力的伟大精妙之处也在于此罢。
我似乎得到了黑暗赐予我的一双夜眼,终于能看清来时的碎石阶了,远处夜游的萤子感觉象是山间朴实人家的灯火,我想,那灯下应有另一个温暖而平淡的故事吧。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股淡淡的清愁,在这苍茫的夜里,真正多情的也许还是自己,毕竟那萤火不是人家的灯火,所有的一切都是沿着既定的轨迹日复一日地演绎着,而我呢?我这样轻轻地问自己。
走在回来的路上,我有种莫名的失落,抬头那繁星在厚实的夜幕中渐次消隐,那月亮钻出云层竟成了大而圆的满月了。我似乎有种微茫的笑意,这样想着,头已经碰到房门了。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走进一片陌生的群山。不知从何时起,我已忘记了儿时数繁星这回事。也许是因为生计困顿罢,这些年尽在纷繁的人事中挣扎、流转,压根就模糊了四季的界线;也许是美的破灭只因距离太近吧没有光环的天使,没有雾岚的鲜花可谓是风景的缺憾。如今,我的心也许老了,在我看来,繁星只不过是宇宙中一团团进行聚变反应的高能量旋转体了。
也许幼年住惯了城市大杂院里漆黑的小阁楼罢,窗外间歇呼啸而过的车辆和夜行人沙沙的脚步,已成为生命中舒缓的摇篮曲。如今在这孤寂的山间夜里,却时常夜半无端地醒来。若是冬夜,还可就着落雪声或风过丛林尖啸声安然入睡,但这静得让人发虚的夏夜,亢奋的夏虫鸣叫似乎太琐碎了。我呆呆地坐在床上想,在这残月光景里,天上的繁星该别有一番意思罢。
沿着碎石阶迂迥而下,随意走进一片杉树林里。我终于又看见幼年时的繁星了!那些似曾相识的精灵们,有的睁着刚睡醒时朦胧的眼;有的喧闹地说,勿忘我;还有些忽隐忽现的,仿佛品味着人生的清凉。一会儿,我视野里繁星渐渐多了起来,有的离我而去。有的正向我飞来。我想,如果站在家里高高的平台上,定能摘到它们。然而,这异乡的土地似乎显得低沉些,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在流动的夜气里显得高耸而怪异。我不怕这夜的狰狞,因为我是爱夜的,爱夜每个有夏虫争鸣的角落,爱每颗灵性的繁星。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满月不见星,残月满天银。我想,眼前这情形应算得上是“满天银”了吧。此刻的月光不象旷野里的那样均匀而单调,而是流动并富于生气的。微风中的树梢摇曳着地上的月光,这微微颤动的亮点真象是抽象派的素描画,可产生天马横空的梦幻,也可让人寂然凝虑的思索。白天这几排经过人工刻意修整的水杉是刚劲质朴的伟丈夫,现在却有着婉若流水般的身影,自然力的伟大精妙之处也在于此罢。
我似乎得到了黑暗赐予我的一双夜眼,终于能看清来时的碎石阶了,远处夜游的萤子感觉象是山间朴实人家的灯火,我想,那灯下应有另一个温暖而平淡的故事吧。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股淡淡的清愁,在这苍茫的夜里,真正多情的也许还是自己,毕竟那萤火不是人家的灯火,所有的一切都是沿着既定的轨迹日复一日地演绎着,而我呢?我这样轻轻地问自己。
走在回来的路上,我有种莫名的失落,抬头那繁星在厚实的夜幕中渐次消隐,那月亮钻出云层竟成了大而圆的满月了。我似乎有种微茫的笑意,这样想着,头已经碰到房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