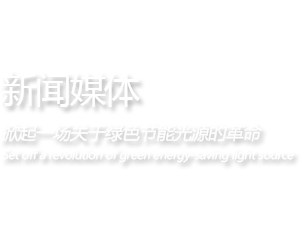兰普集团

新闻媒体

兰普刊物
老师徐徐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30日
“我姓徐,徐徐落幕的徐”。
三年前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正歪着脑袋数着树荫下的斑驳的亮点。阳光里走来一个胖乎乎、矮敦敦戴着眼镜的小男人,他昂首阔步的样子象只饱食后的公鸡。耐不住无聊的我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象看到毛主席那样激情澎湃地说:“欢迎,热烈欢迎徐徐同志加入我们单身汉俱乐部”徐徐这个名字便从我不自觉地引用中叫开了。单身汉们徐徐长,徐徐短地叫着,嘘嘘多了,听着就有上厕所的欲望。
起初,我猜想徐徐肯定是音乐老师。因为每当我用膳、就寝或出恭的时候,楼上爆炸出歌声,激昂时象锯木头,缠绵时象公驴失恋。我经受了个把月的音乐洗礼,揽镜自照竞瘦了一圈。在一个清新的早晨,我终于鼓起勇气对徐徐说:“徐徐老师早上好今天的天气真好你的歌声更好不过你小点声最好你饶了我好不好”“好”徐徐欣然允诺。
楼上约有几天没有传来锯木头或公驴失恋的声音了。为了补回精神上损失,我特意烧了一大碗红烧肉,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独自享用。刚夹起一块还没来得及放进嘴里,背后传来徐徐的歌声,我心跳加速,手一颤,一大碗肉全掉在地上,连碗也破了。回头正看见老师躲在树后深情地歌唱。“喂,您每天都这样教您学生唱歌吗?”“不,我不教音乐,我是个数学老师”徐徐笑得灿若山花。
数学老师面对的是无限的阿拉伯数字,而音乐老师只需读懂七个音符数字。所以数学老师不如音乐老师术业有所专攻,歌声自然也就象锯木头或公驴失恋了。我心里这样想着,也就渐渐平息下来。
后来,我搬到二楼和老师渐渐地熟识起来。可惜,我这大老粗没有艺术细胞。即便是热情如火的夏天,徐徐穿着红裤衩儿,晃着脑袋,有节凑地拍着圆肚皮,对着山凹间凉月象狼一样地歌唱,他似乎大有“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势,而我至多只能算是“泉眼无声惜细流了”。
人是怕寂寞的动物。夏去冬来,转过来年的春天,我和徐徐竟要好的可以共穿一条裤子了。不久就发现徐徐其实是一个很懂生活艺术的人。“学以至用”是他的特点。有一次,他把锅碗瓢盆呈宝塔壮堆积起来,并洋洋自得地说:“这是美观和稳定的最佳结合体。美观因素占68%,稳定因素占领30%,科学创造了美,美遵循着科学”。徐徐习惯性地给我们上起了课,那神情比母鸡下蛋还张狂。第二天我学他的样子“艺术”一回,得意的小曲还没哼完,我的那些锅碗瓢盆便在一片稀里哗啦中变成了一堆碎片。后来,我只好拿着筷子到处借碗吃饭。
关于我的别出心裁,徐徐在“苦中乐”单身汉俱乐部的聚酒会上发表郑重讲话:“科学容不得半点别出心裁。一味地模仿并不符合数理逻辑的规律。正命题为真,反命题就未必真了,比方说吧,我爸爸是个长胡子的男人,但你能说长胡子的男人就我爸爸吗?…”徐徐摇头晃脑地给我们上课,单身汉们笑嘻嘻地附合说,有理,有理!听老师讲课胜读十年半书。
不过徐的数理逻辑也大显神威的时候。有一回,我和徐徐在街上穷逛,只能盯着赏心悦目的小姑娘或闻着餐馆里飘来的香气解馋。我们走到街尾看见一大群人提鸭般地伸着脖子往里看,原来是一个黑胖子满嘴唾沫星子地卖“狗皮膏药”说什么免费抽奖,中奖率是百分之百。我对徐徐说:“咱就试试吧?目前我们也只能挑免费的试了,我发财了肯定不忘记你。”“我就穿一条裤子,呆会儿你把裤子输了,我可没裤子借给你。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中关奖的机会是1/450800,十万分之一都不到。而你输钱的机率却有15876/46189,约占三分之一。”徐徐冷静地回答我说。看着那黑胖子有恃无恐的样子,心里升起一种天降大任的豪情,我竟然走上去揭穿了黑胖子的骗局。黑胖子说:“有人还敢在老虎嘴上拔毛!”“我是武松”徐徐大声地说。
时光飞逝,浓荫夏长时又来了新单身汉。徐徐又自我介绍地说:“我姓徐,徐徐落幕的徐。”
油汗兮兮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文/严国栋)
三年前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正歪着脑袋数着树荫下的斑驳的亮点。阳光里走来一个胖乎乎、矮敦敦戴着眼镜的小男人,他昂首阔步的样子象只饱食后的公鸡。耐不住无聊的我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象看到毛主席那样激情澎湃地说:“欢迎,热烈欢迎徐徐同志加入我们单身汉俱乐部”徐徐这个名字便从我不自觉地引用中叫开了。单身汉们徐徐长,徐徐短地叫着,嘘嘘多了,听着就有上厕所的欲望。
起初,我猜想徐徐肯定是音乐老师。因为每当我用膳、就寝或出恭的时候,楼上爆炸出歌声,激昂时象锯木头,缠绵时象公驴失恋。我经受了个把月的音乐洗礼,揽镜自照竞瘦了一圈。在一个清新的早晨,我终于鼓起勇气对徐徐说:“徐徐老师早上好今天的天气真好你的歌声更好不过你小点声最好你饶了我好不好”“好”徐徐欣然允诺。
楼上约有几天没有传来锯木头或公驴失恋的声音了。为了补回精神上损失,我特意烧了一大碗红烧肉,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独自享用。刚夹起一块还没来得及放进嘴里,背后传来徐徐的歌声,我心跳加速,手一颤,一大碗肉全掉在地上,连碗也破了。回头正看见老师躲在树后深情地歌唱。“喂,您每天都这样教您学生唱歌吗?”“不,我不教音乐,我是个数学老师”徐徐笑得灿若山花。
数学老师面对的是无限的阿拉伯数字,而音乐老师只需读懂七个音符数字。所以数学老师不如音乐老师术业有所专攻,歌声自然也就象锯木头或公驴失恋了。我心里这样想着,也就渐渐平息下来。
后来,我搬到二楼和老师渐渐地熟识起来。可惜,我这大老粗没有艺术细胞。即便是热情如火的夏天,徐徐穿着红裤衩儿,晃着脑袋,有节凑地拍着圆肚皮,对着山凹间凉月象狼一样地歌唱,他似乎大有“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势,而我至多只能算是“泉眼无声惜细流了”。
人是怕寂寞的动物。夏去冬来,转过来年的春天,我和徐徐竟要好的可以共穿一条裤子了。不久就发现徐徐其实是一个很懂生活艺术的人。“学以至用”是他的特点。有一次,他把锅碗瓢盆呈宝塔壮堆积起来,并洋洋自得地说:“这是美观和稳定的最佳结合体。美观因素占68%,稳定因素占领30%,科学创造了美,美遵循着科学”。徐徐习惯性地给我们上起了课,那神情比母鸡下蛋还张狂。第二天我学他的样子“艺术”一回,得意的小曲还没哼完,我的那些锅碗瓢盆便在一片稀里哗啦中变成了一堆碎片。后来,我只好拿着筷子到处借碗吃饭。
关于我的别出心裁,徐徐在“苦中乐”单身汉俱乐部的聚酒会上发表郑重讲话:“科学容不得半点别出心裁。一味地模仿并不符合数理逻辑的规律。正命题为真,反命题就未必真了,比方说吧,我爸爸是个长胡子的男人,但你能说长胡子的男人就我爸爸吗?…”徐徐摇头晃脑地给我们上课,单身汉们笑嘻嘻地附合说,有理,有理!听老师讲课胜读十年半书。
不过徐的数理逻辑也大显神威的时候。有一回,我和徐徐在街上穷逛,只能盯着赏心悦目的小姑娘或闻着餐馆里飘来的香气解馋。我们走到街尾看见一大群人提鸭般地伸着脖子往里看,原来是一个黑胖子满嘴唾沫星子地卖“狗皮膏药”说什么免费抽奖,中奖率是百分之百。我对徐徐说:“咱就试试吧?目前我们也只能挑免费的试了,我发财了肯定不忘记你。”“我就穿一条裤子,呆会儿你把裤子输了,我可没裤子借给你。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中关奖的机会是1/450800,十万分之一都不到。而你输钱的机率却有15876/46189,约占三分之一。”徐徐冷静地回答我说。看着那黑胖子有恃无恐的样子,心里升起一种天降大任的豪情,我竟然走上去揭穿了黑胖子的骗局。黑胖子说:“有人还敢在老虎嘴上拔毛!”“我是武松”徐徐大声地说。
时光飞逝,浓荫夏长时又来了新单身汉。徐徐又自我介绍地说:“我姓徐,徐徐落幕的徐。”
油汗兮兮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文/严国栋)